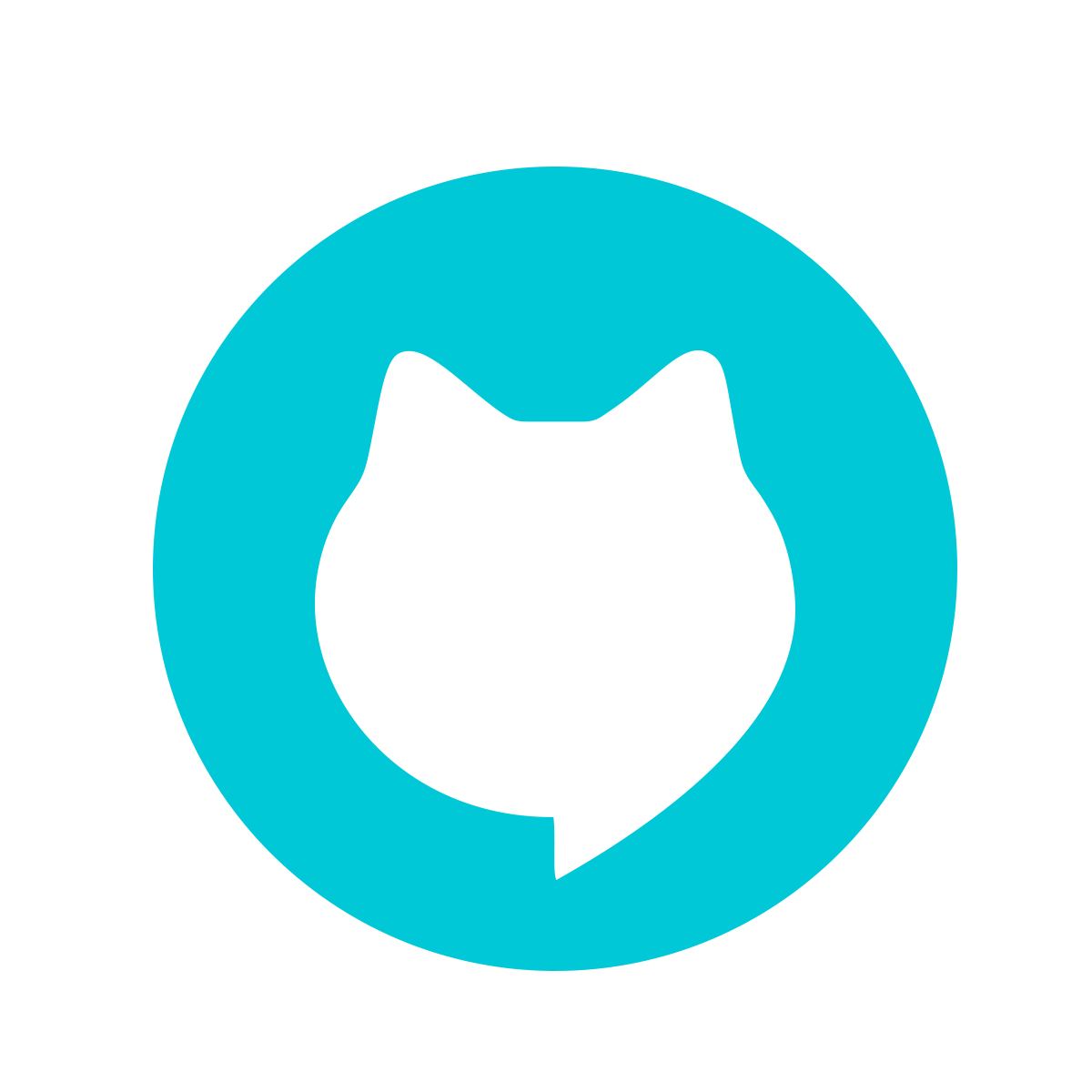- A+
从此世上无大侠,只留经典在人间!到底什么人喜欢读金庸,而金庸群侠传2攻略和穿越金庸世界都被金庸吧的粉丝怀恋。

金庸与浙江的情缘
金庸,不只是一个笔名,是我们共同的时代记忆。“飞雪连天射白鹿,笑书神侠倚碧鸳”……实在不敢相信,陪我们长大的他,真的离开了。
看过金庸小说的人都会好奇,金庸到底跟他笔下的哪个人物比较像。是机灵圆滑的韦小宝?老实憨厚的郭靖?还是优柔寡断的张无忌?
虽然因创作出许多豪气万丈的大侠形象而被称为“查大侠”,但是金庸却觉得这个称谓实在过誉:“如果在我的小说中选一个角色让我做,我愿做天龙八部中的段誉,他身上没有以势压人的霸道,总给人留有余地。”
倪匡曾经评价“段誉有绝顶武功,朱蛤神功好象没有怎么用过,六脉神剑要紧时用不出,斗酒时却大派用场,凌波微步要来作逃命之用,倒十分实在。”在性格上,段誉博学多才、善良固执,被爹娘取小名为“痴儿”。由此看来,段誉的这些特征倒是与金庸有些相似。
金庸本名查良镛,出生在浙江海宁,祖上是名门望族,不但善于经商,而且出了很多学识渊博的后人。
虽然在查良镛出生时家道已经有些衰落,但依然有良田三千亩。男孩子都淘气,但他不同。家里藏书多,他便整天泡在藏书堆里,读得废寝忘食。父亲怕他读出毛病,便想方设法让他出去玩。
有一次,父亲拖他出去放风筝,放着放着,一回头,查良镛不见了。
父亲急得不行:“怕被别人拐走了。”找了半天没找着,回家一看:“这小子正泡在书房看书呢。”
在读书这方面,查良镛也可算是个“痴儿”。但他虽爱书成痴却并不呆板,相反,他还颇有做生意的天赋。其实要论他真正的处女作,并不是武侠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,而是一本叫做《给初中投考者》的试题精编,由查良镛和其他两位同学根据所考的内容自己出题编写。这本试题精编类书籍畅销几省,赚到的第一桶金就足够把他供到大学。那时他只有十五岁。
虽然成绩优异,但查良镛却不是那种“乖乖仔”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“天生自由散漫、不守规矩”。
1940年,查良镛考入浙江联合高中。当时学校常办壁报,文笔极佳又爱好写作的查良镛成为了壁报的常客。有一天,壁报前面挤满了人,大家都在争相看着一篇名为《阿丽丝漫游记》的文章:
“阿丽丝小姐来到校园,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,伸毒舌,喷毒汁,还口出狂言,威吓学生:我叫你永不得超生……”
学生们看了,禁不住哈哈大笑。因为谁都知道眼镜蛇指的就是他们的训导主任,训导主任的名言就是——我叫你永不得超生。
这篇大作的作者就是查良镛。因为看不惯训导主任的种种行径,“瞧不得他有事没事就辱骂学生”,便仗义执言,用笔来讨伐他。
训导主任看到文章,气得全身发抖,立马跑到校长那里哭诉:“请立即开除他。”几天后,查良镛被勒令退学了。他便转到衢州中学,念完了高中。
一个人一生中被开除过一次,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个“传奇人物”,但难就难在还被开除过两次。
查良镛在四川重庆读大学时代,念的是外交系,希望成为一名外交官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。但由于看不惯学校里不良的校风,他再次因大胆直言,于是遭遇了平生第二次开除。外交官理想因此幻灭。
命运有时说来也奇怪,查良镛虽然一生都未实现他的外交官理想,但他后来也说:“虽然没有成为一名外交官,但我并不后悔。我自由散漫的性格确实不适合做这个职业。外交官的规矩太多,说不定做到一周我就被开除了。”
于是命运把他带进了人生的另一个方向。1946年秋天,《大公报》刊登启事: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。应聘者蜂拥而来,竟多达3000人。查良镛凭借自己的才华被千里挑一,进入上海《大公报》,正式步入了报人生涯。
1948年,《大公报》香港版复刊,查良镛被派到香港工作,这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。那时在香港工作并不是一个好差事。跟现在的国际化大都市来比,那时的香港比上海要差得多。但香港在发展,查良镛作为报人、作为金庸的人生也在一步步走上正轨。
1950年,《大公报》旗下《新晚报》创刊,查良镛被调到《新晚报》,做了副刊编辑。
当时《新晚报》总编辑罗孚注意到,比武擂台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。于是灵机一动,决定邀请编辑陈文统在报刊上连载武侠小说。小说连载后引起轰动,自此打开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大门。
这部小说叫做《龙虎斗京华》,陈文统给自己起了个笔名,叫“梁羽生”。
1955年2月初,梁羽生的《草莽龙蛇传》快连载完了,但他还没有想好下一部写什么。
罗孚便只好找到另一个武侠迷查良镛:“梁羽生顾不上了,只有你上了。”
于是查良镛的武侠处女作《书剑恩仇录》问世,反响甚至超过了梁羽生。他将名字最后一字一分为二,署名“金庸”。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,香港的政治风气比较复杂。走到哪里,都是一片说谎声。金庸忍不住了:“我必须发声。”于是,他找到昔日同学沈宝新,两人一起出资,创办了《明报》。
办《明报》要十万块,金庸自己就出了八万。他将自己写小说和稿子赚的钱全部投了进去。他每天一篇的社论,在众多报纸中独树一帜。当时金庸一边写小说,一边写社评,小说要写八九百字,社评要写一千多字。还要随时关注国际时讯,精力消耗很大。每天一睁眼,就有两千字的稿子等着他。晚饭都不吃,要写好社评才能坐下来安心吃饭。社评写完的时候,一般也就到了报纸要发的时候。时常看到金庸在边上写,报纸排字工就站在旁边等着他。
金庸一直持续地为正义发声,也将家国天下的主题融入进小说中,于是便有了《神雕侠侣》《飞狐外传》《倚天屠龙记》……身为持续发出声音的公众人物,金庸必然会被某些势力视为眼中钉。有人放出话来:要消灭五个香港人,排名第二的就是金庸。
金庸说:“我虽然成为暗杀目标,生命受到威胁,内心不免害怕,但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,以至被我书中的英雄瞧不起。”
最危险的一段时间,金庸听到风声,还跑去欧洲躲藏了一个月。连载的《天龙八部》只好找倪匡代笔。一个月后,金庸回到香港。倪匡笑着对他说:“抱歉抱歉,我讨厌阿紫,所以把她的眼睛写瞎了。”
但不屈服的金庸又撰写了政治寓言小说《笑傲江湖》,以及社会问题小说《鹿鼎记》。“为国为民,侠之大者”可谓是金庸的真实写照。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,舆论风气归于平静。1972年,金庸宣布封笔:“如果没有什么意外,《鹿鼎记》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。”
金庸写了十四部武侠小说,部部经典。但金庸的名气虽响彻中外,而且博古通今,历史、政治等知识信手拈来,他依然觉得自己学问不够。因此即使是在获得剑桥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后,金庸坚持选择作为普通学生申请就读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,那时的他已经是81岁高龄。
在剑桥读书时,金庸同普通学生一样。背着双肩包,里面放满了课本。有一段时间金庸还会骑着车上课,但因为太太担心会发生危险而就此作罢。
在剑桥上学,金庸又变成了那个别人不太关注的查先生。不再有知名作家光环、不再是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,他做的一切都“不为学位,只为学问”。
有学生想找金庸拍照,签名。金庸说:“我现在是学生,不是作家。等我不是学生的时候,我再和你坐下来一起吃饭、喝茶。”
在金庸眼里,在任何时候学习都不算晚。永远保持谦卑的态度去探索人生中的未知,自尊而不自负,骄傲而不自满,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必须修炼的一部武功秘籍。
有人曾经问金庸:“人生应如何度过?”老先生答:“大闹一场,悄然离去。”人生在世,去若朝露。一个人的一生,为何不可以是一部武侠小说,前半生纵情恣意、洒脱妄为,后半生心怀敬畏,有不断向学之心。就如查大侠的人生,可敬,可叹。
------皈依佛教与生死问题
池田:适才我们谈过雅戈布列夫先生与佛教的话题。金庸先生也信奉佛教,且对佛学甚有造诣,先生皈依佛教,是缘起于什么事呢?
金庸:我之皈依佛教,并非由于接受了那一位佛教高僧或居士的教导,纯粹是一种神秘经验,而且是非常痛苦和艰难的过程。
池田:请往下说。
金庸:1976年10月,我十九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。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,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。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:“为什么要自杀?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?”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,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。
池田:是吗?我可是初次听到。失去孩子的父母亲的心情只有当事者才可理解。我也是这样,我曾失去我的次子。我的恩师户田先生也有过这样痛苦的经历。他还年轻的时候,他的仅有一岁的女儿夭折了,这是发生在他皈依佛教前的事。他曾经感伤地缅怀道:“我抱着变得冰冷的女儿,哭了整个晚上。”过了不久,他的夫人也撒手人寰,这使得他认真地思考有关“死”的问题。
金庸:此后一年中,我阅读了无数书籍,探究“生与死”的奥秘,详详细细地研究了一本英国出版的《对死亡的关怀》(Man’s Concern with Death)。其中有汤恩比博士一篇讨论死亡的长文,这篇长文有不少精湛的见解,但不能解答我心中对“人之生死”的大疑问。这个疑问,当然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。我在高中时期曾从头至尾精读过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,这时回忆书中要义,反复思考,肯定基督教的教义不合我的想法,后来我忽然领悟到(或者说是衷心希望)亡灵不灭的情况,于是去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。
池田:户田先生也曾在失去长女及妻子之后的一个时期信奉过基督教,但是,关于“生命”的问题,却始终无法令他信服,也无法解答困惑和疑问。您之所以认为基督教不合您的想法,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能解答“生死观”的问题吧!
那次会晤,我们说起过的康丁霍夫·卡列卢基先生曾经说过:“在东方,生与死可说是一本书中的一页。如果翻起这一页,下一页就会出现,换言之是重复新生与死的转换。然而在欧洲,人生好似是一本完整的书,由始而终。”这也就是说,东方与西方的生死观有着本质的不同,对于“生死观”,您曾作过竭力的思考,当然也不会满足于那种将人生视作“一本完整的书”的生死观吧!但是,佛典浩繁,不可能一口气学完,那种苦读和钻研殊非易事啊!
金庸:是啊!中国的佛经卷帙浩繁,有数万卷之多,只读了几本简单的入门书,就觉得其中迷信与虚妄的成分太重,不符合我对真实世界的认识;但还是勉强读下去。后来读到《杂阿含经》、《中阿含经》、《长阿含经》,几个月之中废寝忘食、苦苦研读,潜心思索,突然之间有了会心:“真理是在这里了。一定是这样。”不过中文佛经太过艰深,在古文的翻译中,有时一两个字有完全歧异的含义,实在无法了解。
于是我向伦敦的巴利文学会订购了全套《原始佛经》的英文译本。所谓“原始佛经”,是指佛学研究者认为是最早期、最接近释迦牟尼所说佛法的纪录,因为是从印度南部、锡兰一带传出去的,所以也称为“南传佛经”。大乘佛学者和大乘宗派则贬称之为“小乘”佛经。“原来如此,终于明白了”
池田:能以汉译的佛经与英译的佛经相对照比较,才可以对之进行研究。
金庸:英文佛经容易阅读得多。南传佛经内容简明平实,和真实的人生十分接近,像我这种知识分子容易了解、接受,由此而产生了信仰,相信佛陀(印度语文中原文意义为“觉者”)的的确确是觉悟了人生的真实道理,他将这道理(也即是“佛法”)传给世人。我经过长期的思索、查考、质疑、继续研学等等过程之后,终于诚心诚意、全心全意的接受。佛法解决了我心中的大疑问,我内心充满喜悦,欢喜不尽——“原来如此,终于明白了!”从痛苦到欢喜,大约是一年半时光。
池田:我希望您能原原本本地谈谈当时的心情。
金庸:随后再研读各种大乘佛经,例如《维摩诘经》、《楞严经》、《般若经》等等,疑问又产生了。这些佛经的内容与“南传佛经”是完全不同的,充满了夸张神奇、不可思议的叙述,我很难接受和信服。直至读到《妙法莲华经》,经过长期思考之后,终于了悟——原来大乘经典主要都是“妙法”,用巧妙的方法来宣扬佛法,解释佛法,使得智力较低、悟性较差的人能够了解与接受。《法华经》中,佛陀用火宅、牛车、大雨等等多种浅近的比喻来向世人解释佛法,为了令人相信,甚至说些谎话(例如佛陀假装中毒将死)也无不可,目的都是在弘扬佛法。
池田:《法华经》富于艺术性,有“永恒”,有广阔的世界观、宇宙观,有包容森罗万象一切生命空间的广大。其中许多警句般的经文有影像般的美,简直可以说是一本庄严的“生命的摄影集”,可以一页一页翻转似的,那一瞬一瞬的画面如在眼前浮现。
金庸:我也是了解了“妙法”两字之旨,才对大乘经中充满幻想的夸张不起反感。这个从大痛苦到大欢喜的过程大概是两年。
池田:《法华经》是“圆教”,如果从作为大乘经典最高峰的《法华经》来看的话,其他的佛经,都可谓各执真理一端的说教,一切经全部都可收纳于“圆教”的《法华经》中,宛如“百川归海”。您先学小乘佛经,后再研读大乘经典,得出的结论认为《法华经》是佛教的真髓,这确实反映出先生对于佛教的认真探索之精神。
金庸:对于我,虽然从小就听祖母诵念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、《金刚经》和《妙法莲华经》,但要到整整六十年之后,才通过痛苦的探索和追寻,进入了佛法的境界。
金庸先生曾说过: “研读这些佛经之后,我觉得看待许多事情都变得清朗,连死都不怕了,不再计较名利得失,心里坦荡荡的,无所挂碍。”
先生晚年惟好静,万事不关心。曾有人在报上对金庸的小说进行了刻薄的嘲讽,许多人都以为金庸会大动肝火。但恰恰相反,金庸只是向媒体发了一封特别温和的公开信:“……上天待我已经太好了,享受了这么多幸福,偶尔给人骂几句,命中该有,也不会不开心的。”
轻描淡写的泰然,当真如他小说中《九阳真经》中的几句话:“他强由他强,清风拂山冈。他横任他横,明月照大江。”
他曾提到这样一个例子,到北京来看到一个朋友生活虽不富裕,但一家人和睦相处,其乐融融;而一位香港的朋友虽是家财万贯,却烦恼缠身,不得安逸。他说,“还是北京那个朋友过得好一些。”
在四川走访时,许多读者捧着他的书请求签名,但摆在金庸面前的,几乎都是盗版书。金庸大笔一挥就签了,说:“除了签名,其他都是假的。”如不是对佛学有深入实修实证,怎么说得出如此一般富有禅机的话语?
也许只有看到生死并且堪破了,心上才能真的安,活着才能真的稳。
如果说活着就是一种修行的话,晚年的金庸,真有了“天心月圆、华枝春满”的朗然意韵。
是的,我们忘不了他,如同忘不了心底那个波诡云谲、沧海长啸的武侠世界。他从此离开了这个刀光剑影的娑婆世界,在极乐净土的一端静默微笑,但我们依然可以接通他,那就是跟他一样去深入佛学。